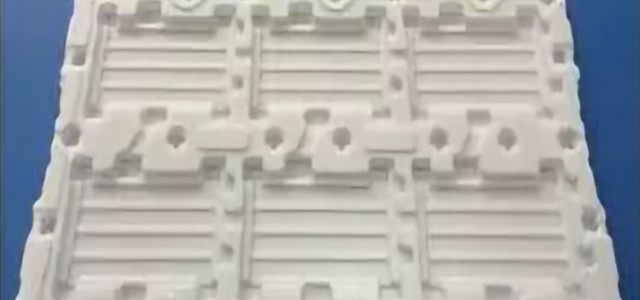退休之后,過士行挺忙的。他得玩兒,客廳的茶桌、書房的書架和書桌,滿滿當當散落著各式的蟲具,上百只蛐蛐罐、蟈蟈筒,他把玩了二十多年。得空兒,他要去十里河蟲市遛遛,挑幾只叫聲清亮的蟈蟈回家。一次,葫蘆蟲具上的小零件壞了,他量了量尺寸,上淘寶一搜,得意地找到了合適的賣家,花十幾塊錢修補好了這上百元的寶貝。
他曾經在舞臺上呈現的作品,如同他的生活,充滿京味兒的語言和樂趣,抖段子的節奏,包袱一拋,臺下笑聲就起。1993年,在北京人藝門口,觀眾排出一里長,一直堵到報房胡同里,就是為了看一場過士行寫的話劇《鳥人》。
上世紀90年代,他作為編劇的閑人三部曲——《魚人》《鳥人》《棋人》大火,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派戲劇史上“過爺”的地位。那時候,他已是知天命之年。姜文看了他的戲,邀請他給自己復出后的首部電影當編劇,于是,有了姜文認為“來勁兒”的《太陽照常升起》。
如今,在霧霾里的北京深冬,過士行閑適地待在通州暖氣充足的住處,十幾只鳴蟲在罐子里的叫聲此起彼伏,仿佛嫁接了一個豐收的秋天。
困惑與開始
在瑞典著名編劇和導演英格瑪·伯格曼的作品《婚姻情境》里重新發現人性的機關時,過士行已經想嘗試導演一部話劇,那是2009年左右。《婚姻情境》曾在1973年于瑞典電視臺播放,是一部六集電視劇,引發眾多討論。之后,伯格曼相繼又創作出了此作品的電影版和話劇版。
等過士行真的作為導演,把它搬上中國話劇舞臺,離他產生做導演的想法又過去了好幾年。打動他的地方與當初第一次看時仍然一樣——故事里的女人在詢問男人,自己是否要生下孩子。伯格曼感嘆,在情感面前,大多數人都是文盲。過士行深以為然。
伯格曼在情感上歷經波折,有過五任妻子,這些感悟被注入作品。話劇舞臺上的人物始終是男女主角兩人,場景就是他們的家或男人的公司,沒有戲劇化的情節,只用兩人的對話,帶出他們的婚姻故事,以及其中瑣碎又致命的問題。
過士行從未感覺生活的細節被如此細膩地展現。“我們從小缺乏愛的教育,只有愛集體,愛事業,但關系到個人、伙伴、異性的愛,都是回避的。”過士行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在這之前,他關注的是社會層面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。比如,北京樹林里的鳥市,精神分析醫師觀察養鳥的人,想要構建自己的學術系統,為此把這里變成了“鳥人心理康復中心”。來到這里的養鳥人只關心鳥,看似關心鳥的鳥類學家卻把珍貴的鳥做成了標本。眾生相在此展開,沒有人關心彼此,沒有人關心人類,這是過士行的困惑。也深深擊中了當年的觀眾。
但他最喜歡的還是《棋人》,關于天才孤注一擲的投入和逃脫不了的宿命。下棋為生的人,棋類的名家,都是過士行再熟悉不過的人,從小看著他們未成大器時的樣子,日后又見到那些人功成名就。他的祖父和叔祖父,就像劇本中的主角,“風度翩翩,白皙的皮膚,修長的身材,從外表到骨子里是天生的儒雅”。
北平解放的時候,圍棋世家從安徽應邀遷居而來,成立北京棋藝研究社——新中國第一個圍棋組織。過士行出生在1952年冬天,家人依據明末的圍棋大師先祖過白齡傳記中,“其人雅馴有士行”一句,為他起了名字。但是,年幼的過士行就發現,自己數學不行,難以深入圍棋之中。最終只走到業余三段。
那時候的他,有自認為頗為神氣的理想。他不止一次想象,自己拿著大銅鈴,吆喝著“倒土”,等垃圾裝好車,車子發動,他就飛身上車,絕塵而去。再長大一些,他喜歡上另一份工作——掏茅房。他就把凳子倒背在自己肩上,假裝是糞桶,手里拿起一個水舀子,喊“廁所有人嗎”,這種時刻,他覺得“其樂融融”。
小學二年級那個寒假,他翻到了《林海雪原》,開始迷上小說。他跑去租書鋪子里,花一分錢,站半天。從《說岳全傳》《楊家將》《海底兩萬里》等中外傳奇,到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起源》,甚至是《胚胎學》。他記得一個戴眼鏡的瘦高店員看見他翻這書,面露憤怒,厲聲問他是哪個學校的,他趕忙逃跑。
看了書,上課的時候就天馬行空地亂想。這一切都給他日后的戲劇寫作隱約打下基礎。那些戲劇中的荒誕和寓言色彩,加以京味兒的相聲式的諷刺,都是小時候對周遭的觀察和各種雜亂閱讀之后的化學反應。
從記者到戲劇
2019年上半年,《鳥人》復排,過士行選角兒,想讓演員即興來一段跟養鳥人的互動,再唱段京劇。來面試的年輕人一一應了要求,最后來了《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》選段,過士行為這字正腔圓的唱腔欣喜叫好。
曲藝的愛好也是自幼的熏陶。父母在銀行當職員,他跟著二姨姥姥長大。二姨姥姥喜聽戲,收音機里每天都是相聲、鼓書。然后再繪聲繪色地講給他聽。他津津有味地聽著,草船借箭的故事里,魯肅在渡江的小船里嚇得哆哆嗦嗦,而諸葛亮氣定神閑地喝起了酒。后來,他跑去翻《三國演義》,怎么也沒找見這個映入腦海的畫面。看了京劇才明白,那是馬派在《群英會》里的演法。
1969年,17歲的過士行去了北大荒。那四年中,只有《復活》一本書是歲月里鮮亮的光,但得等到晚上,把它藏進被子里,才能去讀。那個時候,想著能夠回城當個工人也就滿足了。
后來,他被安排回北京的工廠做車工,負責生產壓面機和電機。他買了書來學技術,在車間練切削工具。舅舅說,這些將來都是要被機器取代的,都會自動化,他便不再上心。開會的時候,領導要人講歷史人物的儒法斗爭,過士行用二姨姥姥那兒聽來的講法,來了一段曹操馬踏青苗的故事,把嚴肅的政治生活弄成了評書演義。講了半小時,他獲得了一個月不用上機床的待遇。
1978年的一天,他在去洗澡的路上,聽見工廠的大喇叭放出《北京日報》招考新聞學員班的消息。同事勸他去試,他感覺胸中有個微弱的火苗在竄起來。考試沒有數學,語文卷子他得了將近滿分。將要26歲的時候,他收到了錄取通知。一年的培訓后,他被分配到《北京晚報》戲劇版。
從那開始,他干了15年記者,看戲成了工作,接觸名家也是工作,每天忙于寫稿,幾乎沒有業余生活,沒時間讀書也沒時間沉淀。工作的模式和路數反反復復,但沒有創作的空間。
因為工作原因,他結識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導演林兆華。1986年,過士行采訪完莎士比亞戲劇節,有了強烈的創作沖動。林兆華鼓勵他,只要你寫出來,我就可以導。他從最熟悉的事情開始,釣魚、逗鳥、下棋。
第一部話劇《魚人》就在1989年春節誕生,花了7天時間寫完。他心里沒底,寫幾句就要給林兆華打去電話,把臺詞念給他聽,怕自己寫出來的不是戲。
后來,林兆華一直認為,過士行語言里有老舍的幽默,還有自己獨到的韻味。當然,對他的戲劇也有批評的聲音傳來,說這就是雕蟲小技,把相聲搬上了戲劇舞臺。過士行倒不以為意。
最終,他決定放棄做記者,轉而正式去寫戲,自己去構造一個比現實過癮的世界,他渴望觀眾。《魚人》《鳥人》《棋人》三部曲完成于90年代初,中國正在經歷巨大的變革,過士行想要寫的,是這種時代環境下夾在著的無形壓抑和對自由的渴望。
“他大概是從有限悲觀走向有限樂觀的狀態”
2009年,過士行轉型做導演,自編自導了話劇《暴風雪》。他自嘲不像林兆華可以找來大腕。以前,《鳥人》的劇本寫好之后交給林兆華,演員陣容就能匯聚起林連昆、何冰、濮存昕、徐帆。
排《暴風雪》的時候,他在北漂里找演員,都是很年輕的孩子。演員劉丹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,“如果我從導演的角度來想,面對這么多新人,會不知道該怎么辦,但是他會利用每個人的優缺點。作為演員,我覺得這種開放性很重要,能建立特別大的空間,還有辦法讓大家成為朋友。”跟過士行認識多年,劉丹覺得,過士行不會過分在意自己的表達要非常具象地呈現,而是會把他的認知藏到細節里,做一些減法。
每次,他們一起喝頓酒,吃頓飯,過士行馬上就樂了。“他很可愛,特別熱愛生活。當代好多知識分子有些沉重的東西,他沒有。他好像可以轉化孤獨和痛苦,知道哪個是不想要的。”劉丹說。
前幾年,過士行的老伴兒生了場病,劉丹看出過士行的著急,覺得自己之前的陪伴少了。身邊的人離世和衰老,讓過士行也流露出了對老之將至的恐懼,他害怕自己的藏物和玩物被別人隨意處置,他放不下這些。
“他大概是從有限悲觀走向有限樂觀的狀態。有限悲觀底色還是偏樂觀的,有限樂觀其實就都是悲觀。”史航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“我覺得老過比以前悲觀得多吧,這也跟時代有關。”
最近,過士行在關注殺醫事件,曾經昌平那邊的拆遷也是他關心的,但這些終究還是成不了他的寫作題材。過士行覺得,已經明知道是非黑白,再去寫,那不高級。如今,再回想起三部曲,過士行仍然覺得自己在戲劇中觸及的問題是無解的。他現在還有困惑想要表達,但創作需要精力和心力,他覺得自己已經寫不動了。他會勸年輕人,有想法就先寫出來,雖然他創作的開始是在37歲,閱歷最盛的時候。“很多東西都有時間限制。就像棋手老了,不是棋藝下降,是精力不夠了。”他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感慨。
周圍的人常會注意到過士行的微信朋友圈,一天會分享好多條,有時候凌晨也在發。除了時事新聞,還有著似乎與他年齡不符的內容,比如一些娛樂八卦。他早已清楚,書店里的信息比不上網絡了,自己眼睛也不太好了,書里的字也不如手機上的字可以調大。朋友圈里三教九流都有,大家每天的分享他都想要翻一翻。
如今,他把書法、篆刻停了一陣,就感覺難再拾起來,因為有人偷魚竿,也不釣魚了。蟲兒和蟲具始終是他沒法放下的樂趣。有一次,他養的蟲兒在劇場不見了,鼓樓西劇場的創始人李羊朵看見他焦急地滿場找,找到之后又重新換上了那副樂樂呵呵的樣子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20年第2期
聲明:刊用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稿件務經書面授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