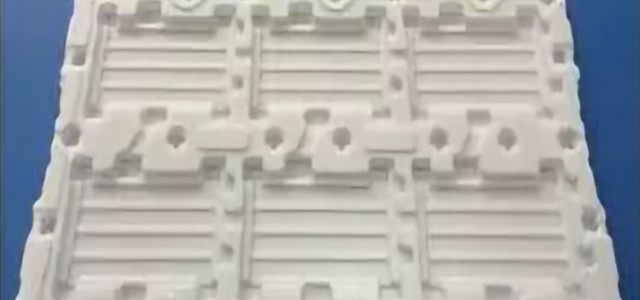原標題: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:關注人的生存恐懼
我們致敬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,致敬它宏大的格局和厚重的內涵;我們更要致敬作者,是他以小說家的勇氣和責任感為我們展現出這幅戰爭圖卷,并讓我們確信:遠離戰爭,不論它以什么名義。
采寫丨張進
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
作者:鄧一光
版本:四川人民出版社
2019年7月
作者簡介
鄧一光
鄧一光,當代作家,著有長篇小說《我是太陽》《我是我的神》等10部,中短篇小說集《懷念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》《狼行成雙》《坐著坐著天就黑了》等20多部。作品大量入選各種年選,并以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、韓、蒙古等文字譯介到海外。曾獲魯迅文學獎、馮牧文學獎、林斤瀾短篇小說杰出作家獎、郁達夫文學獎、國家圖書獎等重要文學獎項,入選收獲文學年度長篇小說榜、當代文學年度長篇小說榜、中國小說學會年度長篇小說榜等重要文學榜單。
致敬辭
戰爭從未遠去,當我們以為它已遠去;歷史從未消逝,當我們以為它已消逝。在耗時五年寫就的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中,鄧一光以嚴謹的態度,在龐雜的史料中挖掘出香港保衛戰的真實細節,又以出色的文學才華和幽微細膩的想象力,對這場戰爭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逼真的再現。鄧一光的寫作焦點并不在于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,而是聚焦于一名普通少尉,一個被囚禁在戰俘營的人。也正是作者對戰俘遭遇的深刻描寫,才讓我們認清人類原本的脆弱,才讓我們真正意識到戰爭對人性的摧殘。
我們致敬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,致敬它宏大的格局和厚重的內涵;我們更要致敬作者,是他以小說家的勇氣和責任感為我們展現出這幅戰爭圖卷,并讓我們確信:遠離戰爭,不論它以什么名義。
答謝辭
這個時代,人們與圖書相逢的機會越來越多,智慧閱讀不再是一個問題,但是,打開的大門也有可能再度關閉,人們需要一種出自對知識和真相本能了解和持續追問的勇氣。《·書評周刊》是閱讀者的領航人,它相信閱讀的力量,從這個意義上講,能夠從它手中領取年度好書獎是莫大的榮幸。謝謝書評周刊,謝謝評委,謝謝讀者!
這本書
“曾一度想放棄,最終堅持下來”
: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700多頁,非常厚重,你在書的末尾列的參考資料也多達47條。創作本書的緣由是什么?寫作過程遇到了怎樣的困難?
鄧一光:說起來很簡單,因為關注了人的小,人的生存恐懼,所以寫了它。這個故事不在我的經驗中,收集資料和做田野調查用了幾年時間,醞釀時間比較長。寫作中有過絕望時刻,曾經一度想過放棄,最終堅持下來了。
:為什么會選擇香港保衛戰作為小說的背景?
鄧一光:這個故事考慮過好幾個背景,歷史敘事中它們都屬于顯題,而我需要找到和主人公一樣被遮蔽或消失掉的背景,所以沒有動筆。大約2013年,那一年發生了很多事情,比如日本決定修改《防衛計劃大綱》并通過了自衛隊法修正案、朝鮮進行了第三次地下核試驗、伊朗核問題六國會議舉行、美國波士頓國際馬拉松賽事期間發生爆炸案、“棱鏡門”事件爆發、日本福島核污水泄漏等等。也就在那一年,我注意到太平洋戰爭中香港這段經歷。香港是中國與西方第一次武裝沖突后割讓的土地,歷史上三度殖民,太平洋戰爭中第一座被攻克的城市,但人們對它的認識卻奇怪地萎縮掉了,具有這個故事需要的多數材質,于是我選擇了它。
:此書在結構上相當特別,用每個人的第一人稱,拼貼出事情的原委。為什么會用這種結構方式?這種結構方式對內容的表達產生了怎樣的效果?
鄧一光:這個故事的敘事任務決定了它不是要尋找一段歷史,而是要重構甚至塑造一段歷史和歷史中人的精神世界,思想、語言、美學和歷史材料必須構成相關整體,傳統的歷史敘事顯然無法完成這一任務。故事提供了10人10種類型的系統性共時講述,重點不在搭建與主人公相關聯系的結構框架,而在于它們形成了單數和復數的人的意識,即思維活動,它們是互為存在的部分,以此構成整體故事的新的意義講述前提。
:主人公郁漱石的身份很值得玩味。為什么把他的身份設定為中日混血?
鄧一光:人們很容易獲得文化和民族的對立或對抗故事,這種二元化的“童話”故事自1842年起講了一百多年,令人沮喪,這種情況,之于個體生命的境遇也是如此。實際上,近代以來人們面對的主要困境不是歷史和文化的純一性,而是歷史和文化的雜糅性,是它們引發的沖突和焦慮,所以,我的主人公需要跨文化和跨血緣的身份設置——實際上,你在近代歷史中能找到大量這樣的例子。
這個人
“不讓我的主人公從視線中消失”
:你的寫作一直關注戰爭,其中的原因有哪些?和你出生于軍人家庭是否有關系?
鄧一光:我的寫作題材相對較寬,戰爭背景的作品是其中一部分,它們受到閱讀者關注,所以一般人認為我只寫戰爭題材作品。
:在60多歲的年齡,還能保持如此強的創造力,寫出了最好的作品之一,你是如何做到的?
鄧一光:
:平時會規定自己每天寫多少字嗎?
鄧一光:沒有特別規定,實際上就算規定了也做不到。寫這部書那段時間,我的第一工作是每天帶母親去公園散步,讓她能快樂地多活幾年。還有,寫這部書過程中我曾一度放下,帶了一個自稱“小懟隊”的青年才俊團隊去做別的事情,大約工作了三四個月,結果失敗了,只能遣散團隊灰溜溜回家繼續寫這個故事。要是規定了字數,我可能是世上最糟糕的寫作者。
這一年
“我希望人們對這個故事有興趣”
:今年《人,或所有的士兵》獲得了很大的關注。這對你意味著什么?
鄧一光:經歷中有過幾次,新鮮勁早已沒有了。我希望人們對這個故事有興趣,如果你說到的關注指這個,我很高興。
:在當下出版有關戰爭
(二戰)
的小說,個中意義有哪些?
鄧一光:
作者丨張進
編輯丨安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