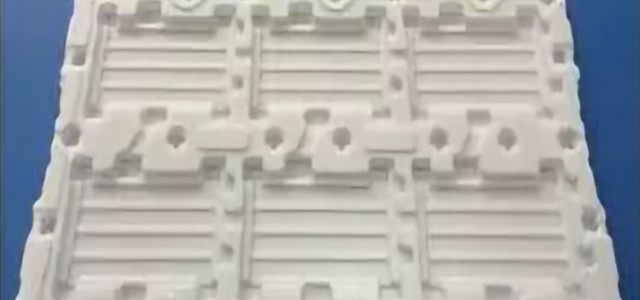原標題:商鞅及其變法的爭議史:從司馬遷到章太炎
從戰國晚期到清末民初,每逢歷史面臨變革,關于商鞅其人其政總會舊話重提。商鞅于公元前四世紀主持的變法,將秦國帶入強國序列。商鞅被車裂的悲慘結局,數千年來一直受人同情。商鞅因何成功,又為何非死不可?在朱維錚看來,需從歷史本身說明商鞅的歷史實相。
很難用幾句話來描述商鞅的為人。
他原是衛國公族的賤支子孫,跑到魏國充當貴族家臣,得知魏王無意用他,又投奔秦國,靠與閹宦拉關系而叩開宮門,這在當時已屬“小人”行為。然而獲得秦孝公信用,他要求法令必行,強調“以刑止刑”,卻以制造恐怖作為“止刑”代價,“步過六尺者有罪,棄灰于道者被刑,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余人,渭水盡赤,號哭之聲動于天地”,甚至民眾改變態度稱贊法令,也被他斥作“亂化之民”,一概流放邊城。他的確打擊了心懷怨望的宗室貴戚,但顯示法無例外的同時,也如前述對帶頭犯法的太子曲為庇護。
按說執法應該無所畏懼,但論者往往忽視司馬遷復述的一個情節,即趙良對商鞅說的:“君之出也,后車十數,從車載甲,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,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。此一物不具,君固不出。”沒有重兵保護,便不敢出門,可見商鞅對自己打造的鐵幕也缺乏信任,如趙良所說“危若朝露”。因而,商鞅在秦行法的主客觀矛盾,便成為后人爭議的歷史問題。司馬遷肯定商鞅變法導致秦人富強,卻否認商鞅為人,說他“少恩”,“其天資刻薄人也”。
《帝制中國初期的儒術》,朱維錚著,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版。本文出自書中《重考商鞅變法》一節。
那以后,關于商鞅的爭論,一度變得很激烈。例如,漢昭帝始元六年
(公元前八一年)
于是,商鞅的變法效應和個人品格,變成是一非二的問題,由此出現的“評價”二元對立,主要體現帝國政權與郡國的利益糾葛。用所謂“儒法斗爭”作為判斷這二元對立的是非基準,是反歷史的。歷史提供的續例,便是擊敗霍光家族的漢宣帝,說是“漢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雜之”,但在意識形態上仍利用而非否定儒學。他親手培養的一名漢家新“儒宗”劉向,便回到司馬遷,宣稱商鞅雖私德有虧而公德可嘉,甚至稱道商鞅自任秦相,便“極身無二慮,盡公不顧私”,所以秦孝公得成戰國霸君,秦歷六世得以兼并諸侯,“亦皆商君之謀也”。
爾后很長時間,商鞅又成治國圖強的一個楷模。三國蜀漢諸葛亮便教訓后主劉禪,要他讀《商君書》。商鞅的法術和人品再度受非議,是在北宋王安石稱道商鞅變法而“百代遵其制”之后。但非商鞅的司馬光,也曾對商鞅信賞必罰作了高度贊揚,而蘇軾否定商鞅的權術,也并非為了“尊儒反法”,相反倒是影射王安石的“尊孟”口是心非。古怪的是,時至南宋,朱熹、陸九淵兩派,都自命“孔孟之道”的原教旨主義者,但都很少提及商鞅其人其法。回避也是一種態度。我曾指出,從程頤到朱熹一派道學家,在政治上都反對王安石變法,在經學上卻屬于王安石新學的“遺囑執行人”。由他們回避對商鞅歷史是非表態,似可為拙說一證。
商鞅。電視劇《大秦帝國之裂變》劇照。
這里不必再提清乾隆間成書的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。其于子部法家類小序,只說刑名之學已為“圣世所不取”,“關于商鞅、韓非諸家,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”,而正文《商子》提要,僅考世傳《商君書》,“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論,以成是編”,暗示內容不可信。
當然,關于商鞅的爭議必將延續。百年前發生戊戌變法,康有為、譚嗣同等痛斥商鞅,表明這回變法并非追求君主專制,卻引發章炳麟力求復原商鞅歷史實相的諫諍。
如今時過境遷,再來討論商鞅變法和他的為人,理當走出忽褒忽貶的傳統循環怪圈。倘能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商鞅的歷史實相,也許更有利于對這段變法史的認知吧?
“孤秦”要圖強
古典中國在公元前五世紀進入戰國時代。顧名思義,這個時代的表征,便是諸侯國之間攻城掠地的戰爭不斷。假如按照司馬光主編的編年史名著《資治通鑒》,將公元前四〇三年東周“天子”承認三晉即韓、趙、魏三國君主為諸侯作為戰國的開端,那么不過三四十年,當時的黃河中下游地區,經過列強兼并戰爭,已形成七雄并立的局面。
七雄即齊、楚、燕、趙、韓、魏、秦七國諸侯,其中唯有秦國在黃河與崤山以西,文明程度較河東和山東六國要低得多。公元前三六二年,二十一歲的秦孝公即位,就面對這樣的列強態勢:“周室微,諸侯力政,爭相并。秦僻在雍州,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,夷翟遇之。”清初王夫之曾說秦國為“孤秦”,看來有歷史理由。
戰國七雄
相傳孔子晚年刪訂的《尚書》,以《秦誓》終篇。《秦誓》的作者秦穆公(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前六二一年在位)曾列名“春秋五霸”。豈料穆公以后,秦國聲價一路下跌,乃至被“中國”諸侯,包括在前曾自居南蠻的楚王,排斥在“中國”以外,被當作夷狄,年輕的秦孝公,憤慨可知,因而即位當年,就公開宣稱志在恢復穆公霸業,“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,吾且尊官,與之分土”。
尊官分土,就是給以高官和封邑。這在春秋時代的霸國已實行,而秦孝公特別聲明要給來自外國的賓客以這類待遇,當然對山東六國的智者,很有吸引力。
果然,秦孝公的通令,引來了一位杰士。他原是衛國公族的遠支,名鞅。成年后跑到魏國,成為執政公叔痤的家臣,自稱衛國公孫,因而稱公孫鞅,又稱衛鞅。相傳公叔痤稱他為“奇才”,臨終曾向魏惠王推薦衛鞅繼其執政,且說如不用就應將衛鞅殺掉。衛鞅逆料魏惠王必謂公叔痤臨死亂命,從容離魏赴秦。
衛鞅入秦,年方“而立”,卻已洞悉宮廷鉆營術。他首先結交秦孝公寵信的宦官,走后門得以見王,然后依次拿出稱帝、稱王、稱霸三種政治設計,逆料孝公必對霸道感興趣。果不其然,秦孝公特別鐘情于他的“強國之術”,“卒用鞅法”。
在秦變法二十年
據司馬遷《秦本紀》,秦自開國,到孝公立,已逾五百年。如此古國,法度傳統早已凝固,“變法”談何容易!好在從秦穆公起,秦國內亂十余世,亂之焦點在于爭奪君位,而君位的吸引力就在于權力獨斷。秦孝公既已掌控獨斷權力,于是以下記載便不奇怪:“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,內務耕稼,外勸戰死之賞罰,孝公善之。甘龍、杜摯等弗然,相與爭之。卒用鞅法,百姓苦之。居三年,百姓便之,乃拜鞅為左庶長。”
需要說明,第一,“百姓”非指庶民,而指“群臣之父子兄弟”。第二,“居三年”,當為秦孝公六年
(公元前三五六年)
(公元前三三八年)
據司馬遷《商君列傳》,衛鞅在秦變法,“行之十年,秦民大說”,于是秦孝公升他為大良造。以后《史記》稱衛鞅二度率軍破魏,還被封于、商洛十五邑,“號為商君”,從此衛鞅被稱作商鞅。但僅過兩年,秦孝公死了,商鞅還能繼續執政嗎?
商鞅在秦國執政期間,曾經兩度頒布變法令。
初令是商鞅任左庶長以后所定,時間在秦孝公六年,當公元前三五六年:
令民為什伍,而相牧司連坐:不告奸者腰斬,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,匿奸者與降敵同罰。
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,倍其賦;有軍功者,各以率受上爵;為私斗者,各以輕重被刑大小;僇力本業,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;事末利及怠而貧者,舉以為收孥。
宗室非有軍功論,不得為屬籍。
明尊卑爵秩等級,各以差次名田宅,臣妾衣服以家次。
有功者顯榮,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。
這道新法令的內涵,顯然是將秦國變成一個軍事化的社會。底層的民,當指對國家承擔納稅服役任務的生產者,都按五口或十口一組重新編制,同一什伍的人口必須互相監視和防范,依照軍紀賞功罰罪。為了保證國家的財源和兵員,強制民間家族拆分為單丁家庭,誰不分家就按男丁數目倍征軍賦。凡從軍殺敵有功的,按照立功大小給予相應的最高爵級,但禁止民間私自械斗,否則依照違反軍紀的程度判刑。
新法令特別重視農工對國家的貢獻,誰納糧交帛超過國家標準,便可免除個人徭役,但誰靠投機取利或懶惰致貧,一旦被檢舉,就要“收孥”即將其妻子沒收充當官奴婢。那么秦國原有的貴族呢?照樣得從軍,即使是公族,沒有軍功,便開除其作為國君親屬的身份,降為平民。
電視劇《大秦帝國之裂變》劇照。
當然,商鞅變法的目的,絕非在一般意義上取消身份、等級及相應特權,而是要將秦國的血統貴族體制,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輩已在局部實施的軍功貴族體制。所以,他取消的貴族特權,只是秦國傳統那種憑借“龍生龍、鳳生鳳”的血親關系就生而富貴的寄生性世襲特權,而代之以軍功“明尊卑爵秩等級”的特權體制。
商鞅這套變法初令,似屬創新,實為復古。還是司馬遷,在《史記》中,不辭辛苦地追尋了秦始皇祖先的發跡史。撇開《秦本紀》開篇的神話,單看兩周之際秦人立國的過程,便可知秦公室鼻祖非子,原是替周天子養馬的家臣,靠牲畜繁殖,而且其后代對付西戎有軍功,于是拜爵封侯。商鞅無非要以嚴刑峻罰和重武賞功相結合的手段,幫助秦孝公實現重振秦穆公霸業的光榮。
怎樣突破行法的雙重阻力?
問題在于商鞅所處的“國際”環境變了。他的圖霸對手,已非仍處于野蠻狀態的西戎,而是文明較諸秦國超勝的“中國”,也就是河東山東的三晉,齊、楚諸侯。更糟的是秦國的宗室權貴,早已被寄生性世襲特權所腐蝕,除了不擇手段地爭權奪利,就極端憎惡變革。當秦孝公被商鞅說服,同意變法,甘龍首先宣稱“知者不變法而治”,杜摯更說:“利不百,不變法;功不十,不易器;法古無過,循禮無邪。”
(見《史記商君列傳》)
因而,秦孝公懷著年輕獨裁者常有的“及其身顯名天下”的沖動,支持商鞅的“強國之術”,卻不能阻止自己的儲君,在宮廷權貴教唆下故意犯法。商鞅明知“法之不行,自上犯之”,卻不敢直接依法處罰太子,“刑其傅公子虔,黥其師公孫賈”。效應看來很好,“明日,秦人皆趨令”。
然而,犯法的是太子,商鞅卻不敢對太子行刑,而向他反對的“六虱”之一儒家所謂“教不嚴,師之過”的荒唐邏輯求助,讓太子的師傅充當替罪羊。諺云“王子犯法,庶民同罪”,道出了民間對法治的理解,所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商鞅初令就宣稱罪與罰必以軍法從事,但逢到太子向他的法度挑戰,就顯得手軟,同樣宣稱支持他行法的太子之父秦孝公,竟示以左庶長執法有例外的處置得當。這不都表明秦孝公用商鞅變法,還是人治高于法治嗎?
商鞅準備變法,最大憂慮,在于預設的變法方案,將受“愚民”的反對。他自居是指導“湯、武不循古而王”的醫國圣手,因而在秦孝公的御前會議上,大發議論,說是“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,論至德者不和于俗,成大功者不謀于眾”。假如這類言論可稱主張“開民智”,那么“愚民政策”一詞,應從古今中外詞典中刪去。
商鞅有沒有讀過《老子》?不詳。但商鞅的確懂得“民之難治,以其智多”,因而他在秦國變法,只許秦民盲目服從,所謂習非成是。當然禁錮民眾頭腦,絕非易事。據司馬遷說,商鞅變法初令頒行,僅秦國都城內謂其不便的公開反對言論,就有上千通。
魏惠王。電視劇《大秦帝國之裂變》劇照。
待商鞅拿太子的師傅當作犯法的教唆犯處置,秦都民眾的確被唬住了,于是被迫守法。如前已述,商鞅的變法初令,追求的效應是在秦國以嚴刑峻罰為手段,強制建立一種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。人人生而屬于某一等級,但允許通過個人從軍殺敵晉爵加級。秦爵的計功原則很簡單,就是“尚首功”,每在戰場上割來一顆敵軍頭顱,便可晉爵一級。雖然將領和士兵的功績計算差異頗大,但社會政治地位的計量尺度為“軍功”,則在秦國已成規矩。這規矩在秦國自上而下說到做到。
相傳商鞅變法初令,“行之十年,秦民大說,道不拾遺,山無盜賊,家給人足。民勇于公戰,怯于私斗,鄉邑大治”。《史記》的這一描述,被研究古典中國改革史的中外學者引了又引。較諸古希臘的梭倫變法,商鞅變法顯得更為成功。以致如今的改革史論者,歷數由王莽改制,到王安石、張居正變法,乃至晚清戊戌變法,認為失敗是改革的宿命,唯有商鞅變法是例外。
我以為以上說法,只是小說家言。小說家值得重視,不僅由于《漢書》已將他們列為九流十家的殿軍,而且因為中世紀眾多小說描述的社會實相,經常映現歷史一枝一節。但倘說時過兩千多年,某部閉門造車的歷史小說,已經復原消逝了的那個帝國全貌,便令人只能目笑存之。
比如商鞅變法,史闕有間,因此成為從漢代司馬遷、宋代司馬光,到清代那一批考史學家,直到清末康有為、譚嗣同、夏曾佑和章太炎等爭論的一個重要課題。至今在中國古史研究中間,仍有爭論。所以要從矛盾的歷史陳述中間清理出歷史事實。
遷都的多重謀慮
說到矛盾的歷史陳述,不妨再引《商君列傳》的續記。秦孝公十五年,當公元前三四七年,衛鞅在秦執政七年了,“于是
(孝公)
然而商鞅卻迅速撤軍,表明他這回出擊魏國,眼光主要在內不在外。從軍事上擊敗強鄰,除了展現秦國已由變法轉弱為強,更可鼓舞秦國民氣,懾服人心,為下一步變法措施減少阻力。證明即破魏以后,他又出“奇計”,就是遷都。秦人“始國”,被周平王封為諸侯,時當公元前七七〇年。那時秦國已從游牧生活轉向定居農耕生活,于公元前八世紀末,在今陜西寶雞東南的平陽筑起都城。不過三十年,便遷都于雍,故址在今陜西鳳翔東南。
又過了近三百年,秦獻公二年
(公元前三八三年)
(公元前三五〇年)
遷都在任何時代都是大事,因為意味著一國的政權、神權連同軍政財政中心大搬家,單是新筑高城深池、宮殿府庫、道路邸宅之類工程,所耗人力、物力、財力便很巨大。秦國居雍已歷十八君三百年,土木朽壞,水源積污。秦獻公棄此舊都,東遷櫟陽,也便于向東擴展,合乎情理。但移都櫟陽不及二世,商鞅就得秦孝公首肯,在咸陽另筑新都,這出于怎樣的需要?
前揭《商君列傳》,記載商鞅攻破魏都安邑而撤軍返秦之后,說:
居三年,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,秦自雍徙都之。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。而集小鄉邑聚為縣,置令、丞,凡三十一縣。為田開阡陌封疆,而賦稅平。平斗桶權衡丈尺。行之四年,公子虔復犯約,劓之。居五年,秦人富強,天子致胙于孝公,諸侯畢賀。
這里所述,與《秦本紀》有出入。后者僅說徙都咸陽,沒說自雍徙之,又謂置大縣四十一,卻漏記禁民父子兄弟同居一室,唯紀年較詳。綜合看來,可知商鞅遷都,主要出于多重的政治考量。秦孝公不是渴望及身“顯名天下”嗎?“都者國君所居”,商鞅無疑要滿足主公心愿,首先在新都起造宏偉的宮殿。宮外迎面便是巍峨相對的兩座樓觀,中間大道兩旁有君主教令。這即所謂冀闕,又稱象魏或魏闕。宮內又是格式齊整的堂寢正室。君主居此,豈不威名遠揚!
李悝《法經》不是告誡需要改變舊染污俗嗎?秦人與西戎雜居,顯然還保留游牧生活那種全家男女老幼共居帳幕的積習。定居后父母兄弟妯娌同室寢處,難免出現聚麀亂倫。既遷都而建新居,商鞅下令禁止一家各對夫婦“同室內息”,應說促進文明教化。
用不著再說廢“封建”而立郡縣的歷史意義。商鞅將小鄉邑合并為大縣,由國家直接派官治理,等于取消了宗室貴族對采邑的等級統治特權。因而以往貴族領地的邊界“草萊”,就變成官府控制的空荒地,允許農民開墾,納糧服役都交付國家。這不僅使賦稅有章可循,也減少了領主的中間盤剝。
還有統一度量衡,同樣使農民工匠感到負擔平均,減少因賦稅不均而引發的社會沖突。傳世文物有商鞅量,又名商鞅方升,上刻秦孝公十八年
(公元前三四四年)
(公元前二二一年)
電視劇《大秦帝國之裂變》劇照。
所以,歷史效應表明,商鞅遷都是有深謀的。他首先滿足秦孝公對生前贏得霸主權威的欲望,當然意在借權變法。他接著借遷都迫使秦國宗室貴族脫離權力基地,乘后者在新都立足未穩,取締他們“有土子民”的傳統特權,當然還保證他們只要擁護新體制,仍可衣租食稅。他同時企圖借遷都使庶民營造新家的機會,改變底層社會的戎俗,但直到兩千年后,陜甘寧貧民依然因饑寒而全家擠睡一室熱炕,證明他這一禁令很難實現。他所謂“開阡陌封疆”,固然使墾田和賦稅的數字增加,但國富民窮適成反比。由一個半世紀后,強權較諸商鞅更有力的秦始皇甫死,被驅迫為國家服勞役的陳涉一伙農民,便扯起反旗,即可知商鞅急法的真正效應。
商鞅因造反被車裂是事后追加罪名?
商鞅遷都咸陽以后,“公子虔復犯約,劓之”?劓刑,即割掉鼻子,相傳為虞舜想改卻改不掉的五刑之一,在肉刑中算是較輕的。不過沒了鼻子,誰看見便知此人是罪犯。公子虔既是秦國宗室,又做過秦太子傅,即訓導官,在前已代太子受黥刑,臉上刺了字,這時又觸犯商鞅某種約束,失去了鼻子,更見不得人。時間大概在秦孝公十六年
(公元前三四六年)
這表明,商鞅盡管將秦國貴族遷到咸陽,但彼輩身在魏闕,心在故都。作為老權貴的領袖,公子虔再度以身試法。這遞送的反面信息,不消說是他們的群體仍在抵制這個外來人在本國搞亂固有的秩序。
商鞅不知他面對的秦國宗室貴族抵制變法么?不然。前揭《商君列傳》說到“商君相秦十年,宗室貴戚多怨望者”之后,就追述趙良見商君的對話。
這個趙良,顯然也是異國入秦的游士,卻對商鞅被封商君
(秦孝公二十二年,公元前三四〇年)
公元前三三八年,秦孝公死了:
太子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,發吏捕商君。商君亡至關下,欲舍客舍。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,曰:“商君之法,舍人無驗者坐之。”商君喟然嘆曰:“嗟乎!為法之敝一至此哉。”
那以后,商君在魏秦間逃亡,找不到歸宿,于是跑回商邑,發兵準備北赴鄭國,卻被秦兵越境殺死。“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,曰:‘莫如商君反者!’遂滅商君之家。”
假如司馬遷所記商鞅的末路屬實,那么只能說這是正言若反。第一,證明商鞅法令已貫徹到秦國邊境,因而旅舍主人見商鞅拿不出通行證,便拒絕他投宿。第二,證明商鞅到自己的封邑發兵,無非借以保護自己流亡鄭國,而秦惠王派兵越境追殺,恰好反證商鞅沒有反秦。第三,證明秦軍殺害商鞅后,才將他五馬分尸,因而作為“公子虔之徒”的秦惠王宣稱商鞅因造反才被車裂,可謂事后追加罪名。
司馬光說商鞅成功在重“信”
早在公元前二世紀中葉或稍晚,《史記》作者司馬遷給商鞅立傳,便寫了一個故事:
令既具,未布,(鞅)恐民之不信,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,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,予十金。民怪之,莫敢徙。復曰“能徙者予五十金”。有一人徙之,輒予五十金,以明不欺。卒下令。
據《史記》司馬貞索隱,“秦以一鎰為一金”。秦衡以二十四兩為一鎰,五十金合秦制黃金一千二百零四兩。如此重賞,表明商鞅頒布變法初令,認定取信于民是令行禁止的首要條件。
時過千余年,與司馬遷并稱中世紀中國史學巨匠“兩司馬”的司馬光,是北宋王朝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領袖,但他在獻給宋神宗的編年史巨著《資治通鑒》開卷第二篇中,照錄了《史記》關于商鞅“樹木立信”的故事,然后大發議論,不妨錄以備考:
臣光曰:夫信者,人君之大寶也。國保于民,民保于信,非信無以使民,非民無以守國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,霸者不欺四鄰,善為國者不欺其民,善為家者不欺其親。不善者反之,欺其鄰國,欺其百姓,甚者欺其兄弟,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,下不信上,上下離心,以至于敗。所利不能藥其所傷,所獲不能補其所亡,豈不哀哉!
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,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,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,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。此四君者,道非純白,而商君尤稱“刻薄”,又處戰攻之世,天下趨于詐力,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,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!
司馬光以史論為政論,借古史教訓北宋六世青年皇帝,重申孔子所謂治國三原則,即寧可去食去兵,也要說話算話,“民無信不立”。
那政論的是非屬于另一問題。這兩段引語至少表明,自秦漢到唐宋列朝統治者形成一個共識,就是內政外交都依賴一個“信”字。信者,誠也。《論語》開篇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語錄,便出現了六個“信”字,特別強調“信近于義”,足證在商鞅以前許多年,無論人際關系還是國際關系,相互信任已是交友結盟、治民睦鄰的第一要義。
商鞅不是法治理論的首倡者,卻是法治實踐的表率。他在秦行法,逢到太子犯法,也曾困惑過,卻在向人情讓步的同時,還是力求護法。倘注意他歸罪于的太子教唆犯公子虔,是秦孝公的庶兄,便可知對此人施以黥刑,在秦國特權貴族中引發的恐懼。
商鞅變法成功的訣竅,如清末章太炎哀悼戊戌變法失敗所著《商鞅》一文所論證的,是商鞅已意識到法是制度的總稱,變法就是變革傳統政治體制,因而法立就不容動搖退縮,“雖乘輿亦不得違法而任喜怒”。在這里,應說秦孝公值得稱道。因為他任用商鞅變法以后,在秦史上便似乎銷聲匿跡,令人感到商鞅已成僭主,視國君如傀儡。只有當他英年早逝,秦國政局徙變,權勢顯赫的國相商君竟然棄職潛逃,人們才得知這位秦孝公是商鞅變法的權力推手,沒有孝公就沒有商君。
所以,商鞅變法,首重取信于民,體現秦孝公賦予商鞅信任為先決條件。中國史家常常悲嘆“人亡政息”,從商鞅在秦孝公死后,立即由叱咤風云的權相化作自己炮制體制的最大犧牲品,或可對這個體制的可“信”度,有深一度的了解。
商鞅為何非死不可
商鞅死了,商鞅在秦國兩度變法的效應,仍在發酵。這就引出另一個問題,商鞅為何非死不可?
沒有了秦孝公的權力支持,固然使商鞅頓失怙恃,但商鞅不是已將秦國變成一個大兵營嗎?秦孝公當然是統帥,但商鞅是久已實權在握的總參謀長。孝公死,太子立,統帥易人,意味著統帥的侍從大換班,但正式相秦已逾十年的商鞅,權勢怎會頃刻瓦解?唯一解釋,只能是商鞅沒有掌握實權。他將秦國軍事化,自上而下灌輸“以力兼人”的理念,所實行的一切變革,都以樹立君主權威為鵠的。秦孝公很樂意享受君主權威節節高的尊榮。因而商鞅的實權,是將君權絕對化為資源,說穿了便是狐假虎威。一旦虎威易主,新狐代替舊狐,商鞅不落荒而逃,才是怪事。
前引趙良痛說商鞅投機史,說他巴結宦官起家,相秦后又“不以百姓為事”,極力討好秦王,與秦國貴公子為敵,“是積怨畜禍也”。所謂“恃德者昌,恃力者亡”,“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”,你商君還不立即被“收”?那時秦孝公才年逾不惑,商鞅有理由不信趙良警告。
豈知商鞅才獲封于、商洛十五邑,“南面而稱寡人”,未及兩年,秦孝公便死了,他立即成為公子虔團伙的緝捕對象。在商鞅被五馬分尸以后七十二年,荀況自秦返趙,與趙孝成王及臨武君“議兵”,陳述在秦觀感,便說出了對秦昭王及其相范雎沒有直說的話,以為秦國不足畏。理由呢?據荀況說,秦國由孝公到昭王四世,君臣唯知“以力兼人”,受害的首先是秦國士民。他們普遍畏懼權威,盡管人人都有“離心”,卻聽從當局驅使,充當對外攻城掠地的工具,“是故得地而權彌輕,兼人而兵愈弱”。
因而荀況便說出那段千古傳誦并引發不絕爭議的名言:
故曰:以德兼人者王,以力兼人者弱,以富兼人者貧,古今一也。
本文選自《帝制中國初期的儒術》中《重考商鞅變法》一節,較原文有刪節調整,部分小標題為編者所擬,非原文所有。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。
作者丨朱維錚
摘編丨何安安
編輯丨楊司奇
校對丨劉軍